GNU和自由软件运动记事(202x)
本文主要用于记录GNU和自由软件一事记,截止2030年之前。
1983年9月27日,计算机科学家 Richard Matthew Stallman(简称 RMS)宣布开发类 Unix 自由软件操作系统的「GNU 计划」,并借此发起自由软件运动,GNU 名字代表 GNU's not Unix。

「GNU 计划」标志
粗略来讲,一个软件如果是自由软件,这意味着用户可以自由地运行、拷贝、分发、学习、修改并改进该软件。因此,「自由软件 (Free Software)」中的 "free" 是关乎自由的问题,与价格无关,软件如何定价并不影响它是否被归类为自由软件。具体来说,自由软件的用户拥有四项基本自由:
0) 自由运行软件
1) 自由学习和修改软件源代码
2) 自由发布软件拷贝
3) 自由发布修改后的软件版本
GNU 是唯一专门为捍卫用户自由而开发的操作系统,多年以来始终忠于其创始理念。自 1983 年以来,「GNU 计划」为私有操作系统提供了合乎道德的完整替代方案。这要归功于世界各地的 GNU 开发志愿者四十年来的不懈努力。除了技术,GNU 还开创性地提出了 "Copyleft"。Copyleft 是源自自由软件运动的概念,是一种利用现有著作权体制 (Copyright) 来保护所有用户和二次开发者的自由的授权方式。
Copyleft 中的 "Left",不使用英语中 “保留” 的意思,而是指 “Left(左)”,与 “版权 (Copyright)” 中的 “Right(右)” 具有镜像的关系。注意,Copyleft 不是反著作权运动,不主张废止著作权,也不是公有领域 (Public Domain)。二者的区别可总结为:"Copyright" 指软件的版权和其它一切权利归软件作者所私有,用户只有使用权,没有其它如复制、重新修改发布等权利。而 "Copyleft" 的特点是仅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其他一切权利可以与任何人共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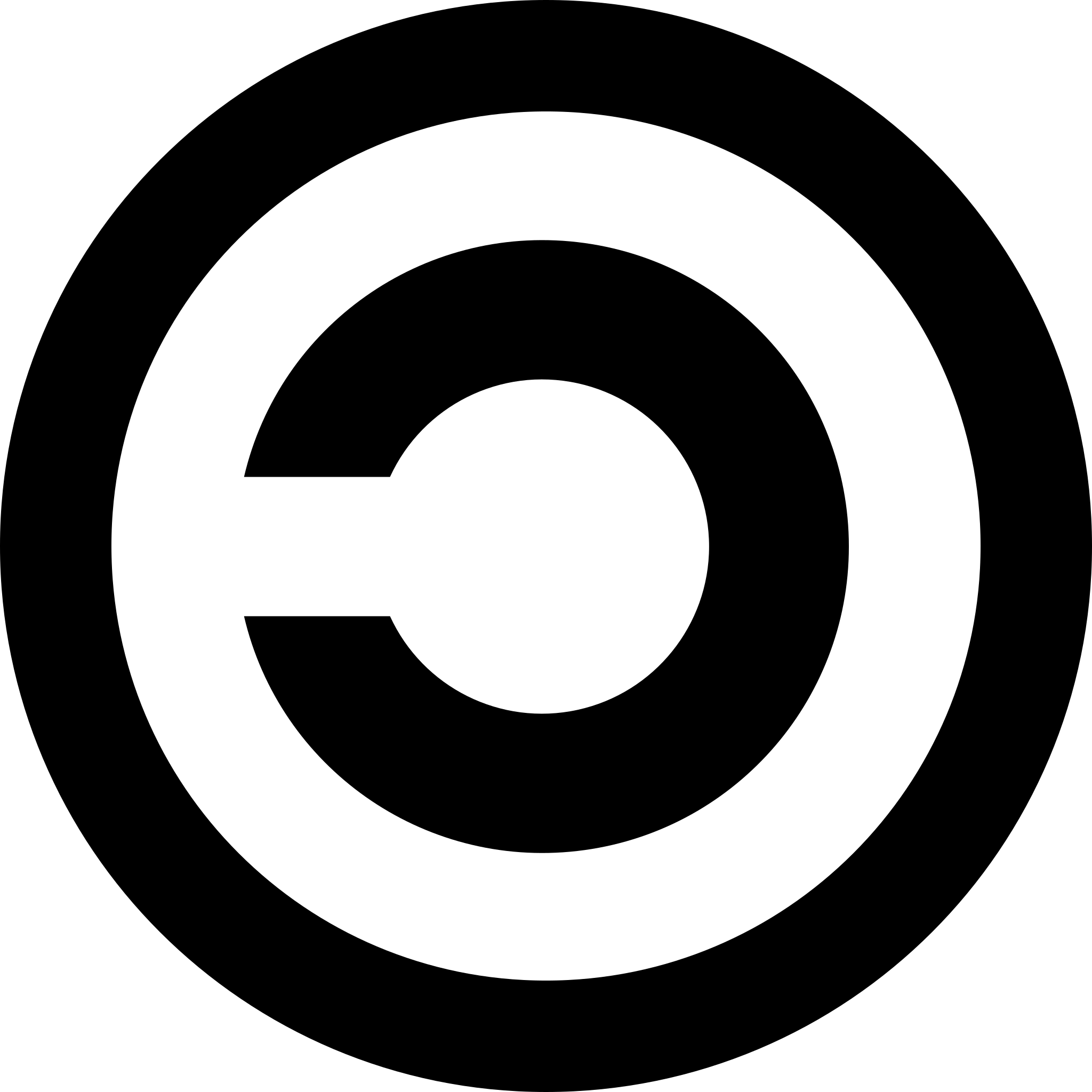
Copyleft 标志
《BSD与Linux的那些事》一文中就将GNU与Linux、甚至开源社区的相关关系阐述比较清楚了。
几个星期前在考虑写点什么关于自由软件基金会三十周年庆,以及它如何给计算机行业的局面带来深远影响。

为了来点真材实料,我要采访John Sullivan,自由软件基金会的执行总监。本来我打算以我惯有的风格行文:饶有趣味的叙述性文字为主,穿插以采访片段作为补充。当我从John处拿到这份详尽而极富洞见的采访稿时,马上打消了这种念头。我决定把采访内容完整地呈现出来作为文章主体,然后再辅以一些评论。这样的话文章会很长,但我觉得唯有这样,才能将这个组织的伟大和迷人之处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我建议你去拿杯美味的饮料,坐下来好好阅读。
时间之沙
自由软件基金会成立于1985年。当时的计算机行业是这样一幅景象——Amiga 1000计算机刚刚发布,C++正在成为主流语言,Aldus PageMaker也刚刚发布译者注:Aldus后与Adobe合并,互联网则刚刚开始发展。哦对了,那个年代,威猛乐队Wham!的名曲《无心快语Careless Whisper》正红极一时。
三十年世事变迁。回到1985年,那时自由软件基金会主要专注于开发一些只有计算机怪咖才会用的软件,而时至今日,我们则需要通盘考虑软件、服务、社交网络以及其他很多东西。
首先我想了解一下,John认为如今的软件自由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当今计算机用户的自由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我想大家都有广泛的共识,只是可能叫法不一而已。”
“第一件事情,我们可能也称之为‘微型计算机无处不在’。自由软件运动已经成功地把完全免费的操作系统带到笔记本、台式机和服务器上,而且功能上完全不输任何商业系统。当然,还有少数的领域没有覆盖到,但也快了。商业软件公司依靠数以亿计的市场推广费用和有利于他们的法律制度,还在不断把商 业软件送到用户手中,这算是我们在这方面依然面临的挑战。”
“然而,我们在微型计算机领域却遇到了严重的问题。这类系统包括手机、平板、眼镜、手表等等,汽车虽然看起来不小,但它里面的计算机系统很小,所以我也把它算在内。这类计算机系统通常使用自由软件作为其运行的基础——举个例子,Android或GNU底下运行的是Linux内核。但这里,Linux内核主要用来支撑商业软件的运行,而这些商业软件则作为基础来连接远程服务,用云计算来替代本地计算。这些设备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些设备为大量人口提供通讯服务,有些设备和我们的身体紧密联系,和我们的重大设施紧密联系,有些设备承担着保护我们人身安全的责任,鉴于此,这些设备必须运行完全自由的软件系统,它们的用户必须能完全掌控它们。但是现在,情况并不是这样。”
John觉得平台和设备尺寸不是主要的风险,关键是所集成的服务。
“我们面临的第二大威胁就是这些设备所连接的服务。如果真正的工作和娱乐都在某家公司运营的远程服务器上进行,我们根本无法染指,那么,本地装一个自由操作系统又有什么意义呢?自由软件的真正意义在于我们可以看到、修改和分享代码。这些自由保证了我们不受某些公司控制,哪怕对不懂技术的用户 亦是如此。如果你使用Facebook、Salesforce或Google Docs,你没什么自由可言。更使人担忧的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种趋势,人们为了获得服务,已经对私有软件强加给他们电脑的限制视而不见了。各种浏览器 ——包括Firefox——都会强行安装一个DRM插件,就是为了迎合Netflix和其他视频行业巨头。我们要更努力地工作,为媒体发行领域开发出可以独立运行的自由软件替代品,给用户、艺术家或兼有两者身份的人们带来强大的生产力。对于其他类型的服务,我们也有此期待。针对Facebook,我们有 GNU social、pump.io、Diaspora、Movim以及其他项目。针对Salesforce,我们有CiviCRM。针对Google Doc,我们有Etherpad。媒体方面,我们有GNU MediaGoblin。但所有的这些项目都需要帮助,而且还有很多商业服务,尚无可与之竞争的替代品。”
John提到了为当下流行的应用和服务开发自由软件替代品,这挺有意思的。自由软件基金会维护了一张“高优先级项目”列表,名单上在列的项目,即是为了达到此目的。不幸的是,这些项目的质量良莠不齐,而且,在社交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软件本身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真正的挑战在于说服人们去用 它。
这些都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在当代的计算机世界中,自由软件基金会的定位在哪里?我是自由软件基金会的粉丝,我认为他们的工作很有价值,我也给他们提供过资助。他们是一家致力于创建开放式计算文化的重要组织,但任何组织都需要成长、调整和适应,尤其是技术圈里的那些。
我想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如今的自由软件基金会,在做哪些当初他们不曾做过的事情?
“我们的受众远多于三十年前,而且也更多元化。了解自由软件,不再仅是黑客、开发者和研究人员的事情,每个计算机用户都会了解,并且很快,每个人都会拥有计算机。”
接着,John以一些例子来说明他们所做的尝试。
“我们正在举办公开宣传活动,来阐述自由软件运动所关切的问题。在成立之初,我们就这些问题表达过看法,并且对其中很多问题有所行动。而近十年来,我们花了更多的精力来规划和举办宣传活动。在数字“限制”管理领域译者注:即数字版权管理DRM,全称是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但本文中写的是Digital Restrictions Management,这是自由软件从业者嘲讽DRM的常见说法,我们发出了震耳发聩的反对声,为此我们建立了“Defective by Design”网站,苹果在iTunes中放弃DRM,我相信这个网站是起了作用的当然,在最新的Apple Music中,DRM又回归了。我们为不了解自由软件的人们准备了引人入胜的介绍性资料,比如我们的《解放用户》动画视频以及《电子邮件自我防御指南》。
我们也支持尊重用户自由的硬件产品。经自由软件基金会认证的硬件产品,可以打上我们的徽标,表明它可以完全使用自由软件来工作。自由软件用户和自由软件运动的基础,可分为两部分:说服人们关注自由,然后使其有所行动。在这种精神下,我们鼓励硬件制造商做正确的事,让那些开始关注自由软件的用户们能买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免去长时间折腾之苦。我们已经认证了家用WiFi路由器、3D打印机、笔记本电脑和USB无线网卡,更多的认证也在进行中。
我们正在为几个自由软件项目提供资助,帮助他们募得开发所需的资金。大多数项目都是GNU的一员我们一直为GNU提供各种基础设施,但我们也赞助了Replicant,这是一个完全自由的Android发行版,把当前最自由的移动设备带给用户。译者注:Replicant基于著名的第三方Android版本CyanogenMod,替换了每个私有组件,包括用户空间程序、库以及固件。
我们在帮助开发者正确地使用开源许可证,也在跟进一些关于公司不遵守GPL条款的投诉。我们帮他们改正错误,正确地传播软件。RMS译者注:即Richard Stallman早年也致力于此,当时GPL尚未成型,而如今,这已经成为我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今天,自由软件基金会所做的大多数事情,三十年前都不曾做过,但早年立下的愿景却从未变过——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世界,在其中,用户在任何计算机上想做的任何事,都可以用自由软件来完成;在其中,用户控制计算机,而不是被计算机控制。”
个性文化
自由软件基金会带来的价值,几乎无人质疑。如John强调的那样,它不仅在自由软件的创建和许可证方面取得了成就,更是在技术领域认同、证明和宣传一种自由文化。

自由软件基金会的领导人是特立独行的Richard M. Stallman,通常叫他RMS。

RMS是个奇人。他对自己的理想和哲学有难以置信的热情,他全身心地信仰软件自由。
但是他在社交方面的弱点也时常在网上遭揶揄,他演讲中的那些话,他对旅行的古怪要求,其他一些令人尴尬的时刻,以及他对软件和自由的固执看法,都会成为理由。他坚守自己的观点。毫无疑问他是个认真的思想家,这种认真不仅是对待自己的想法,更是对待他所领导的广泛运动。我唯一对他持批评态度的一点,他时常会口无遮拦,嘴瘾过足了,好事也变坏事了。不过,嘿,鉴于他对这个世界的重要性,我情愿忍受他的缺点。好吧,这里搞得有点紧张了。
所以RMS是自由软件基金会的关键人物,但是这个组织远不止他一个人。它有雇员、董事会和许多贡献者。我很好奇RMS近期在自由软件基金会里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John和我分享了他的看法。
“RMS是自由软件基金会的总裁,但他干这份工作不领一分钱薪水。他继续着他艰苦卓绝的全球演讲计划,每年他都会在很多国家宣传自由软件和计算机用户的自由。在这过程中,他会见政府官员,也会见搞各种社会运动的本地活动家。此外,他还会为自由软件基金会募集资金,招募志愿者。”
“在这些活动中,他对自由软件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预测了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这通常会催生一些文章——今年早些时候,他给Wired网站写了一系列文章,共有三篇,讨论了自由软件和自由硬件的设计——以及会主导自由软件基金会未来项目的一些理念。”
当我们俩探究个性文化的时候,我想了解John对“自由软件运动传播有多广泛”这个问题如何看。
我记得在Open Source Think Tank一个各种开源组织的主管参加的聚会活动上举行过一个案例研究会,会上各参会人被问及某个特定项目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开源许可证,大多数讨论小组认为Apache Software LicenseAPL要好过GNU Public LicenseGPL。
这件事情在我脑海中久久无法挥去。从那时候起,我意识到很多公司似乎都选择了更开放的许可证,而不是GPL。我很好奇John是否也注意到APL要压过GPL一头的趋势。
“有吗?我不确定。几年前我在FOSDEM上做了一个演讲,题为‘Copyleft在被诬陷吗?’,其中谈及了,许可证选择变化趋势的数据是有点问题的。很快我会发表一篇有关这个的文章,这里我先谈谈几个主要的问题:
自由软件许可证的选择脱离不了具体的背景。如果人们真想得出个结论,那要把选择私有许可证的因素也考虑进去。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选择更宽松的开源许可证比如APL或BSD只是为了替代私有许可证,而不是替代GPL。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统计许可证的人并没有把他们用于统计的工具作为自由软件发布。这意味着我们无法审查他们的统计方法,无法重现结果。目前已经有人公开了他们所用的代码,但是那些不愿意公开的人应该受到鄙视。科学自有它的规则。
什么样的软件有资格被统计呢?如果一个APL授权的软件只是用来发出点搞笑的噪音,它能和GPLv3授权的GNU Emacs相提并论吗?如果不能,我们如何确定不同软件的权重?我们只统计真正能工作的软件吗?我们确定没有重复计算多个站点运行同一软件的情况?操作系 统的不同移植版本,又怎么算?
推敲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但目前我看到的所有结论都言之过早,缺乏确凿的数据。我更愿意看到在开发人员中间做个调查,我们应该问他们为什么给自己的项目选择了某个特定的许可证,而不要写程序去获取软件的许可证情况,然后再对统计数据的规律做牵强附会的解释。
Copyleft一如既往地富有生命力。宽松许可证授权的软件也算是自由软件,表面上看也是不错的。但这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些软件必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确保自身不被商业软件利用。因为,如果自由软件带来的主要长期影响是帮助那些公司更高效地生产出限制我们自由的产品,那么我们在计算机用户自由方面的努力将毫无意义。”
在新的挑战中崛起
历经三十年依然充满活力,对于任何组织来说都不容易,而自由软件基金会要跨越多个行业、专业、政府和文化来实现它的宏伟目标,坚持三十年更是令人钦佩。
访谈接近尾声时,我想更好地理解一下,在履行使命长达三十年后,今天自由软件基金会的主要职能又是什么?
“我认为自由软件基金会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它既坚如磐石,又敢于打破常规。”
“我们有核心的文件,比如自由软件定义、GPL,以及我们维护的自由及非自由许可证列表,这些文件已经是如今自由软件大厦的基石。人们信任我们,所以相信这些文件所宣扬的信条,所以才会把这些原则正确地、聪明地运用到新产品评估和计算机实践中。做个比喻,如果有人想登高,我们就帮他们扶着梯子。作为一家事关公众利益的非盈利组织,我们85%的经费都来自于个人捐助,我们要合理安排资源。”
“但我们也会打破常规。别人认为太难的挑战,我们会去承担。我觉得这好像意味着我们自己也会去造梯子?或许我不该再用这个比喻了。”
虽然John好像不是运用比喻的高手我也不是,但自由软件基金会却擅长为自己设定目标并对此倾尽全力。这种使命来自于信仰——“自由软件应无处不在”。
“如果你说你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大部分都能使用自由软件来工作,但少数组件除外,我们对此结果不会满意。如果你说你有一台平板电脑,可以跑一大堆自由软件,只不过网络通讯的时候,播放视频的时候,拍照的时候,网上值机的时候,用Uber订车的时候需要用点私有软件……好吧,我们对此趋势当然不会满意。如果有人劝我们应该对此满意,我们对这种建议也非常不满意。系统中装任何私有软件,对用户都是不公平的,这本质上是对用户的一种威胁。在通向 自由世界的路上,这些半吊子自由系统的存在或许有其合理性,但我们绝不能止步不前。”
“在自由软件基金会成立早期,我们确实有必要编写一个自由操作系统。现在,GNU、Linux和其他很多协作者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当然软件是永远写不完的,bug也永远修复不完。”
John所指的挑战中,关键一点就是,把正确的硬件交到正确的人手中。
“我们目前最关注的事情,也就是我在第一个问题中所强调的挑战。我们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都急需可以彻底支持自由软件的硬件。在自由软件基金会,我们已经就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谈了很多,我期待我们能有重大的进展,一方面是加大对一些现有项目的支持力度——通过‘尊重您的自由Respects Your Freedom’认证项目,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另一方面也可以创建一些我们自己的项目。云服务的问题也是如此。我想我们需要一起来解决它们。如果我们能完全掌 控移动组件,这将改变我们和云服务之间的关系,而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开发更多的独立移动组件。”
“自由软件基金会在发展壮大,在迎接挑战,希望大众能给我们支持。编写可用、独立并能互相配合的移动组件来代替云服务很有难度,但要搞来足够的硬件也不容易,因为硬件很贵。我们需要很多人为我们贡献资源和聪明才智。三十年前,以RMS为核心,共同抱着以Copyleft的理念去编写一个完整操作系统的理想,一个社区成立了。近十二年我都在为自由软件基金会服务,因为我坚信,我们能以同样的方式,在新的挑战中崛起。”
最后的想法
我咀嚼着John对我的问题深富洞见的回答,同时回想起结识的很多自由软件基金会成员,深深引起我共鸣的是自由软基金会激荡和长存的满腔热情。这个组织丝毫没有对自己的使命感到厌倦甚至幻灭,它的激情和信仰一如既往。
有时候我并不能完全认同自由软件基金会,因为他们的行事方法有点一厢情愿,但尽管如此,我会一如以往地做它的粉丝,支持它的工作。自由软件基金会代表了当下世界自由软件和开源运动的道德心声。它所代表的世界观不容于“左”派,然而它的激情和坚定的信仰,也能感染偏“右”的人们,使他们向“左”靠译者注:“左”的价值观支持平等、大政府干预,“右”的价值观支持个体自由、小政府,自由软件基金会从追求的目标来看,无疑是偏“右”的。但与此同时,变革为“左”,保守为“右”,从这一点来看,自由软件基金会追求目标的热情,无疑是“左”的体现。
诚然,RMS是个怪人,有时候很强硬,有时候又有点令人动容。但在这样一场集技术、道德和文化于一体的运动中,领导人舍他其谁。我们需要 Torvalds译者注:Linux内核作者、Shuttleworth译者注:Ubuntu母公司Canonical创始人、 Whitehurst译者注:Red Hat CEO、ZemlinLinux基金会执行总监,我们也需要RMS。这些性格迥异的人联手为我们描绘了一副未来的远景,展示未来我们会有一门技术,它适用于绝大多数使用场景,并满足绝大多数道德诉求和雄心壮志。
末了,我想感谢自由软件基金会巨大的付出,我祝愿它和它两位无所畏惧的领袖Richard M. Stallman和John Sullivan在下一个三十年中再打一场漂亮的仗。去干吧!
上文是作者Jono Bacon发表在Opensource.com上的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30 years in
GNU和自由软件运动四十周年
自由软件基金会 (FSF) 于2023年9月27日发表文章庆祝 GNU 和自由软件运动四十年。
四十年后的今天,GNU 和自由软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虽然软件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但绝大多数用户无法完全控制它。自由软件的定义最初由 RMS 本人制定。但其初衷是尊重用户的自由,并且尊重整个社区。
FSF 执行董事 Zoë Kooyman 表示,GNU 不仅仅是基于自由软件的最广泛使用的操作系统,也是指导自由软件运动四十年的哲学理念的核心。他还说道,我们希望四十周年纪念能够激励更多黑客加入 GNU,实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创建、改进和共享自由软件的目标。如今,软件正在控制我们的世界,而 GNU 是对现状的批判和解决方案,我们亟需它来避免技术控制人类。
RMS 谈 AI、Red Hat 和道德软件许可
在2023年9月瑞士 Biel 举行的庆祝 GNU 诞生 40 周年的活动上,GNU 和 FSF 创始人 Richard Stallman (RMS) 发表了 25 分钟的演讲,除了披露身患癌症外,他还谈论了 Red Hat、AI 和道德软件许可。

RMS 在瑞士 Biel 参加庆祝 GNU 40 岁生日的活动
他表示目前正在接受滤泡性淋巴瘤的治疗,称之为 “生长缓慢和可控的”。
Red Hat 和 GPL
Red Hat 的支持合同禁止客户重新分发该公司的开源软件,RMS 认为此举可能没有违反 GPL 许可,但其做法是 “反社会的”。他认为红帽公司应该停止这一做法,或者社区能通过施加影响力让 Red Hat 做出改变。
生成式 AI 不具备理解能力
对于 AI 或生成式聊天机器人 ChatGPT,RMS 认为危险主要来自于 AI 营销人员所编织的叙事。他认为今天的 AI 尚未真正具有理解能力,但人们正使用 AI 这一术语来夸大其词,他说 ChatGPT 生成的内容都是废话,不过是流畅的废话。因此他认为,相信 ChatGPT 这类产品生成的内容的人都很愚蠢。
RMS说道:“在我看来,‘intelligence’意味着需要具备了解或理解某个领域的能力。如果某些东西不能真正理解事情,我们不应该说它是智能的,甚至是一点智能都没有,但人们正在用人工智能一词来描述废话生成器。”所以他没有把那些产品称作 “人工智能” 或任何带有 ‘intelligence’ 一词的东西,因为这会鼓励大众认为它们(生成式人工智能程序)所说的不是胡说八道。它鼓励大众相信它们,这给了他们造成巨大伤害的机会。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 RMS 认为真正的人工智能并不存在。他补充到:“有些程序可以查看一些放大细胞的照片并告诉你诊断结果,无论是否患有癌症,比任何人类医生都更有可能正确。另外,有一些人工智能系统可以非常有效地找出什么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这些被反社交媒体平台使用,可悲的是,它们效果很好。他们非常擅长这些工作,但他们所做的是让用户上瘾。”
道德软件许可证
RMS 似乎不是所谓的 “道德” 软件许可证的支持者,试图监管谁可以使用软件。这不足为奇,因为他倡导的自由软件哲学的四项基本自由中的第一项是用户具有出于任何目的运行软件的自由。
演讲最后,RMS 抛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让年轻人对自由软件感兴趣?”他称这个问题是 “我们在社区中面临的难题之一”。
自由软件基金会迎来 40 周年:新任主席上任、推出 “LibrePhone” 计划
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FSF)在 2025 年 10 月迎来成立 40 周年纪念,并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领导层更替与全新自由软件项目的启动。

FSF 任命资深成员 Ian Kelling 为新任主席,他表示将带领基金会应对计算机用户自由面临的新挑战,并扩大自由软件运动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执行总监 Zoë Kooyman 公布了名为 “LibrePhone” 的新项目,目标是在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上实现完全自由的软件系统,为用户带来真正不受限制的计算体验。该项目由长期参与 GNU 开发的工程师 Rob Savoye 参与领导,被视为 FSF 推进 “移动端自由” 战略的重要一步。活动中,来自 EFF、F-Droid、Sugar Labs 等组织的代表共同讨论了自由软件、隐私保护及教育应用的未来合作方向。
FSF 表示,未来将进一步支持全球的地方性自由软件社区(LibreLocal),继续推动用户 “使用、学习、修改与分发” 软件的权利。四十年后的今天,这一理念依旧是自由软件运动的核心。
1983年9月27日,计算机科学家 Richard Matthew Stallman(简称 RMS)宣布开发类 Unix 自由软件操作系统的「GNU 计划」,并借此发起自由软件运动,GNU 名字代表 GNU's not Unix。

「GNU 计划」标志
粗略来讲,一个软件如果是自由软件,这意味着用户可以自由地运行、拷贝、分发、学习、修改并改进该软件。因此,「自由软件 (Free Software)」中的 "free" 是关乎自由的问题,与价格无关,软件如何定价并不影响它是否被归类为自由软件。具体来说,自由软件的用户拥有四项基本自由:
0) 自由运行软件
1) 自由学习和修改软件源代码
2) 自由发布软件拷贝
3) 自由发布修改后的软件版本
GNU 是唯一专门为捍卫用户自由而开发的操作系统,多年以来始终忠于其创始理念。自 1983 年以来,「GNU 计划」为私有操作系统提供了合乎道德的完整替代方案。这要归功于世界各地的 GNU 开发志愿者四十年来的不懈努力。除了技术,GNU 还开创性地提出了 "Copyleft"。Copyleft 是源自自由软件运动的概念,是一种利用现有著作权体制 (Copyright) 来保护所有用户和二次开发者的自由的授权方式。
Copyleft 中的 "Left",不使用英语中 “保留” 的意思,而是指 “Left(左)”,与 “版权 (Copyright)” 中的 “Right(右)” 具有镜像的关系。注意,Copyleft 不是反著作权运动,不主张废止著作权,也不是公有领域 (Public Domain)。二者的区别可总结为:"Copyright" 指软件的版权和其它一切权利归软件作者所私有,用户只有使用权,没有其它如复制、重新修改发布等权利。而 "Copyleft" 的特点是仅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其他一切权利可以与任何人共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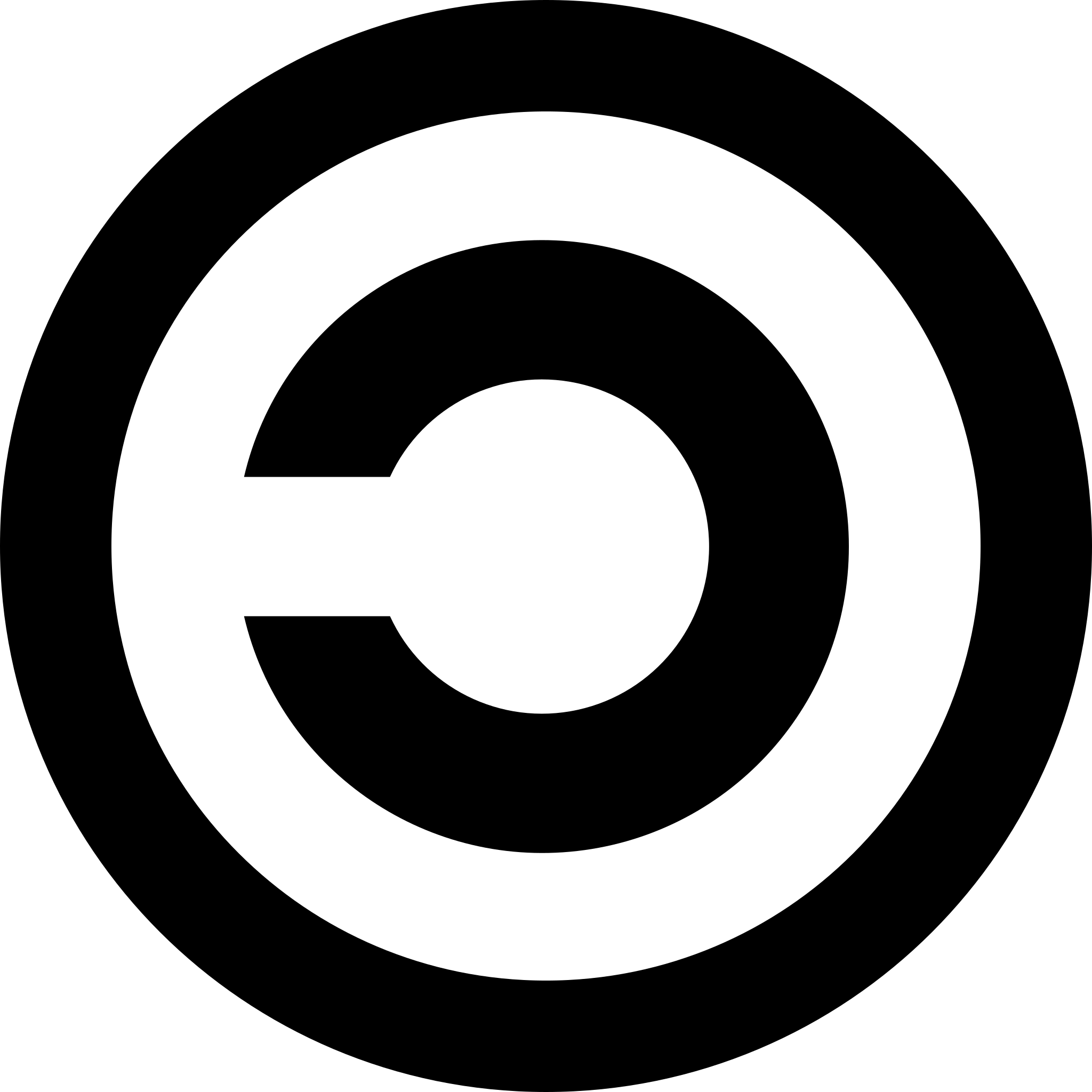
Copyleft 标志
《BSD与Linux的那些事》一文中就将GNU与Linux、甚至开源社区的相关关系阐述比较清楚了。
几个星期前在考虑写点什么关于自由软件基金会三十周年庆,以及它如何给计算机行业的局面带来深远影响。

为了来点真材实料,我要采访John Sullivan,自由软件基金会的执行总监。本来我打算以我惯有的风格行文:饶有趣味的叙述性文字为主,穿插以采访片段作为补充。当我从John处拿到这份详尽而极富洞见的采访稿时,马上打消了这种念头。我决定把采访内容完整地呈现出来作为文章主体,然后再辅以一些评论。这样的话文章会很长,但我觉得唯有这样,才能将这个组织的伟大和迷人之处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我建议你去拿杯美味的饮料,坐下来好好阅读。
时间之沙
自由软件基金会成立于1985年。当时的计算机行业是这样一幅景象——Amiga 1000计算机刚刚发布,C++正在成为主流语言,Aldus PageMaker也刚刚发布译者注:Aldus后与Adobe合并,互联网则刚刚开始发展。哦对了,那个年代,威猛乐队Wham!的名曲《无心快语Careless Whisper》正红极一时。
三十年世事变迁。回到1985年,那时自由软件基金会主要专注于开发一些只有计算机怪咖才会用的软件,而时至今日,我们则需要通盘考虑软件、服务、社交网络以及其他很多东西。
首先我想了解一下,John认为如今的软件自由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当今计算机用户的自由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我想大家都有广泛的共识,只是可能叫法不一而已。”
“第一件事情,我们可能也称之为‘微型计算机无处不在’。自由软件运动已经成功地把完全免费的操作系统带到笔记本、台式机和服务器上,而且功能上完全不输任何商业系统。当然,还有少数的领域没有覆盖到,但也快了。商业软件公司依靠数以亿计的市场推广费用和有利于他们的法律制度,还在不断把商 业软件送到用户手中,这算是我们在这方面依然面临的挑战。”
“然而,我们在微型计算机领域却遇到了严重的问题。这类系统包括手机、平板、眼镜、手表等等,汽车虽然看起来不小,但它里面的计算机系统很小,所以我也把它算在内。这类计算机系统通常使用自由软件作为其运行的基础——举个例子,Android或GNU底下运行的是Linux内核。但这里,Linux内核主要用来支撑商业软件的运行,而这些商业软件则作为基础来连接远程服务,用云计算来替代本地计算。这些设备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些设备为大量人口提供通讯服务,有些设备和我们的身体紧密联系,和我们的重大设施紧密联系,有些设备承担着保护我们人身安全的责任,鉴于此,这些设备必须运行完全自由的软件系统,它们的用户必须能完全掌控它们。但是现在,情况并不是这样。”
John觉得平台和设备尺寸不是主要的风险,关键是所集成的服务。
“我们面临的第二大威胁就是这些设备所连接的服务。如果真正的工作和娱乐都在某家公司运营的远程服务器上进行,我们根本无法染指,那么,本地装一个自由操作系统又有什么意义呢?自由软件的真正意义在于我们可以看到、修改和分享代码。这些自由保证了我们不受某些公司控制,哪怕对不懂技术的用户 亦是如此。如果你使用Facebook、Salesforce或Google Docs,你没什么自由可言。更使人担忧的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种趋势,人们为了获得服务,已经对私有软件强加给他们电脑的限制视而不见了。各种浏览器 ——包括Firefox——都会强行安装一个DRM插件,就是为了迎合Netflix和其他视频行业巨头。我们要更努力地工作,为媒体发行领域开发出可以独立运行的自由软件替代品,给用户、艺术家或兼有两者身份的人们带来强大的生产力。对于其他类型的服务,我们也有此期待。针对Facebook,我们有 GNU social、pump.io、Diaspora、Movim以及其他项目。针对Salesforce,我们有CiviCRM。针对Google Doc,我们有Etherpad。媒体方面,我们有GNU MediaGoblin。但所有的这些项目都需要帮助,而且还有很多商业服务,尚无可与之竞争的替代品。”
John提到了为当下流行的应用和服务开发自由软件替代品,这挺有意思的。自由软件基金会维护了一张“高优先级项目”列表,名单上在列的项目,即是为了达到此目的。不幸的是,这些项目的质量良莠不齐,而且,在社交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软件本身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真正的挑战在于说服人们去用 它。
这些都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在当代的计算机世界中,自由软件基金会的定位在哪里?我是自由软件基金会的粉丝,我认为他们的工作很有价值,我也给他们提供过资助。他们是一家致力于创建开放式计算文化的重要组织,但任何组织都需要成长、调整和适应,尤其是技术圈里的那些。
我想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如今的自由软件基金会,在做哪些当初他们不曾做过的事情?
“我们的受众远多于三十年前,而且也更多元化。了解自由软件,不再仅是黑客、开发者和研究人员的事情,每个计算机用户都会了解,并且很快,每个人都会拥有计算机。”
接着,John以一些例子来说明他们所做的尝试。
“我们正在举办公开宣传活动,来阐述自由软件运动所关切的问题。在成立之初,我们就这些问题表达过看法,并且对其中很多问题有所行动。而近十年来,我们花了更多的精力来规划和举办宣传活动。在数字“限制”管理领域译者注:即数字版权管理DRM,全称是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但本文中写的是Digital Restrictions Management,这是自由软件从业者嘲讽DRM的常见说法,我们发出了震耳发聩的反对声,为此我们建立了“Defective by Design”网站,苹果在iTunes中放弃DRM,我相信这个网站是起了作用的当然,在最新的Apple Music中,DRM又回归了。我们为不了解自由软件的人们准备了引人入胜的介绍性资料,比如我们的《解放用户》动画视频以及《电子邮件自我防御指南》。
我们也支持尊重用户自由的硬件产品。经自由软件基金会认证的硬件产品,可以打上我们的徽标,表明它可以完全使用自由软件来工作。自由软件用户和自由软件运动的基础,可分为两部分:说服人们关注自由,然后使其有所行动。在这种精神下,我们鼓励硬件制造商做正确的事,让那些开始关注自由软件的用户们能买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免去长时间折腾之苦。我们已经认证了家用WiFi路由器、3D打印机、笔记本电脑和USB无线网卡,更多的认证也在进行中。
我们正在为几个自由软件项目提供资助,帮助他们募得开发所需的资金。大多数项目都是GNU的一员我们一直为GNU提供各种基础设施,但我们也赞助了Replicant,这是一个完全自由的Android发行版,把当前最自由的移动设备带给用户。译者注:Replicant基于著名的第三方Android版本CyanogenMod,替换了每个私有组件,包括用户空间程序、库以及固件。
我们在帮助开发者正确地使用开源许可证,也在跟进一些关于公司不遵守GPL条款的投诉。我们帮他们改正错误,正确地传播软件。RMS译者注:即Richard Stallman早年也致力于此,当时GPL尚未成型,而如今,这已经成为我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今天,自由软件基金会所做的大多数事情,三十年前都不曾做过,但早年立下的愿景却从未变过——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世界,在其中,用户在任何计算机上想做的任何事,都可以用自由软件来完成;在其中,用户控制计算机,而不是被计算机控制。”
个性文化
自由软件基金会带来的价值,几乎无人质疑。如John强调的那样,它不仅在自由软件的创建和许可证方面取得了成就,更是在技术领域认同、证明和宣传一种自由文化。

自由软件基金会的领导人是特立独行的Richard M. Stallman,通常叫他RMS。

RMS是个奇人。他对自己的理想和哲学有难以置信的热情,他全身心地信仰软件自由。
但是他在社交方面的弱点也时常在网上遭揶揄,他演讲中的那些话,他对旅行的古怪要求,其他一些令人尴尬的时刻,以及他对软件和自由的固执看法,都会成为理由。他坚守自己的观点。毫无疑问他是个认真的思想家,这种认真不仅是对待自己的想法,更是对待他所领导的广泛运动。我唯一对他持批评态度的一点,他时常会口无遮拦,嘴瘾过足了,好事也变坏事了。不过,嘿,鉴于他对这个世界的重要性,我情愿忍受他的缺点。好吧,这里搞得有点紧张了。
所以RMS是自由软件基金会的关键人物,但是这个组织远不止他一个人。它有雇员、董事会和许多贡献者。我很好奇RMS近期在自由软件基金会里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John和我分享了他的看法。
“RMS是自由软件基金会的总裁,但他干这份工作不领一分钱薪水。他继续着他艰苦卓绝的全球演讲计划,每年他都会在很多国家宣传自由软件和计算机用户的自由。在这过程中,他会见政府官员,也会见搞各种社会运动的本地活动家。此外,他还会为自由软件基金会募集资金,招募志愿者。”
“在这些活动中,他对自由软件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预测了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这通常会催生一些文章——今年早些时候,他给Wired网站写了一系列文章,共有三篇,讨论了自由软件和自由硬件的设计——以及会主导自由软件基金会未来项目的一些理念。”
当我们俩探究个性文化的时候,我想了解John对“自由软件运动传播有多广泛”这个问题如何看。
我记得在Open Source Think Tank一个各种开源组织的主管参加的聚会活动上举行过一个案例研究会,会上各参会人被问及某个特定项目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开源许可证,大多数讨论小组认为Apache Software LicenseAPL要好过GNU Public LicenseGPL。
这件事情在我脑海中久久无法挥去。从那时候起,我意识到很多公司似乎都选择了更开放的许可证,而不是GPL。我很好奇John是否也注意到APL要压过GPL一头的趋势。
“有吗?我不确定。几年前我在FOSDEM上做了一个演讲,题为‘Copyleft在被诬陷吗?’,其中谈及了,许可证选择变化趋势的数据是有点问题的。很快我会发表一篇有关这个的文章,这里我先谈谈几个主要的问题:
自由软件许可证的选择脱离不了具体的背景。如果人们真想得出个结论,那要把选择私有许可证的因素也考虑进去。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选择更宽松的开源许可证比如APL或BSD只是为了替代私有许可证,而不是替代GPL。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统计许可证的人并没有把他们用于统计的工具作为自由软件发布。这意味着我们无法审查他们的统计方法,无法重现结果。目前已经有人公开了他们所用的代码,但是那些不愿意公开的人应该受到鄙视。科学自有它的规则。
什么样的软件有资格被统计呢?如果一个APL授权的软件只是用来发出点搞笑的噪音,它能和GPLv3授权的GNU Emacs相提并论吗?如果不能,我们如何确定不同软件的权重?我们只统计真正能工作的软件吗?我们确定没有重复计算多个站点运行同一软件的情况?操作系 统的不同移植版本,又怎么算?
推敲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但目前我看到的所有结论都言之过早,缺乏确凿的数据。我更愿意看到在开发人员中间做个调查,我们应该问他们为什么给自己的项目选择了某个特定的许可证,而不要写程序去获取软件的许可证情况,然后再对统计数据的规律做牵强附会的解释。
Copyleft一如既往地富有生命力。宽松许可证授权的软件也算是自由软件,表面上看也是不错的。但这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些软件必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确保自身不被商业软件利用。因为,如果自由软件带来的主要长期影响是帮助那些公司更高效地生产出限制我们自由的产品,那么我们在计算机用户自由方面的努力将毫无意义。”
在新的挑战中崛起
历经三十年依然充满活力,对于任何组织来说都不容易,而自由软件基金会要跨越多个行业、专业、政府和文化来实现它的宏伟目标,坚持三十年更是令人钦佩。
访谈接近尾声时,我想更好地理解一下,在履行使命长达三十年后,今天自由软件基金会的主要职能又是什么?
“我认为自由软件基金会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它既坚如磐石,又敢于打破常规。”
“我们有核心的文件,比如自由软件定义、GPL,以及我们维护的自由及非自由许可证列表,这些文件已经是如今自由软件大厦的基石。人们信任我们,所以相信这些文件所宣扬的信条,所以才会把这些原则正确地、聪明地运用到新产品评估和计算机实践中。做个比喻,如果有人想登高,我们就帮他们扶着梯子。作为一家事关公众利益的非盈利组织,我们85%的经费都来自于个人捐助,我们要合理安排资源。”
“但我们也会打破常规。别人认为太难的挑战,我们会去承担。我觉得这好像意味着我们自己也会去造梯子?或许我不该再用这个比喻了。”
虽然John好像不是运用比喻的高手我也不是,但自由软件基金会却擅长为自己设定目标并对此倾尽全力。这种使命来自于信仰——“自由软件应无处不在”。
“如果你说你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大部分都能使用自由软件来工作,但少数组件除外,我们对此结果不会满意。如果你说你有一台平板电脑,可以跑一大堆自由软件,只不过网络通讯的时候,播放视频的时候,拍照的时候,网上值机的时候,用Uber订车的时候需要用点私有软件……好吧,我们对此趋势当然不会满意。如果有人劝我们应该对此满意,我们对这种建议也非常不满意。系统中装任何私有软件,对用户都是不公平的,这本质上是对用户的一种威胁。在通向 自由世界的路上,这些半吊子自由系统的存在或许有其合理性,但我们绝不能止步不前。”
“在自由软件基金会成立早期,我们确实有必要编写一个自由操作系统。现在,GNU、Linux和其他很多协作者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当然软件是永远写不完的,bug也永远修复不完。”
John所指的挑战中,关键一点就是,把正确的硬件交到正确的人手中。
“我们目前最关注的事情,也就是我在第一个问题中所强调的挑战。我们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都急需可以彻底支持自由软件的硬件。在自由软件基金会,我们已经就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谈了很多,我期待我们能有重大的进展,一方面是加大对一些现有项目的支持力度——通过‘尊重您的自由Respects Your Freedom’认证项目,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另一方面也可以创建一些我们自己的项目。云服务的问题也是如此。我想我们需要一起来解决它们。如果我们能完全掌 控移动组件,这将改变我们和云服务之间的关系,而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开发更多的独立移动组件。”
“自由软件基金会在发展壮大,在迎接挑战,希望大众能给我们支持。编写可用、独立并能互相配合的移动组件来代替云服务很有难度,但要搞来足够的硬件也不容易,因为硬件很贵。我们需要很多人为我们贡献资源和聪明才智。三十年前,以RMS为核心,共同抱着以Copyleft的理念去编写一个完整操作系统的理想,一个社区成立了。近十二年我都在为自由软件基金会服务,因为我坚信,我们能以同样的方式,在新的挑战中崛起。”
最后的想法
我咀嚼着John对我的问题深富洞见的回答,同时回想起结识的很多自由软件基金会成员,深深引起我共鸣的是自由软基金会激荡和长存的满腔热情。这个组织丝毫没有对自己的使命感到厌倦甚至幻灭,它的激情和信仰一如既往。
有时候我并不能完全认同自由软件基金会,因为他们的行事方法有点一厢情愿,但尽管如此,我会一如以往地做它的粉丝,支持它的工作。自由软件基金会代表了当下世界自由软件和开源运动的道德心声。它所代表的世界观不容于“左”派,然而它的激情和坚定的信仰,也能感染偏“右”的人们,使他们向“左”靠译者注:“左”的价值观支持平等、大政府干预,“右”的价值观支持个体自由、小政府,自由软件基金会从追求的目标来看,无疑是偏“右”的。但与此同时,变革为“左”,保守为“右”,从这一点来看,自由软件基金会追求目标的热情,无疑是“左”的体现。
诚然,RMS是个怪人,有时候很强硬,有时候又有点令人动容。但在这样一场集技术、道德和文化于一体的运动中,领导人舍他其谁。我们需要 Torvalds译者注:Linux内核作者、Shuttleworth译者注:Ubuntu母公司Canonical创始人、 Whitehurst译者注:Red Hat CEO、ZemlinLinux基金会执行总监,我们也需要RMS。这些性格迥异的人联手为我们描绘了一副未来的远景,展示未来我们会有一门技术,它适用于绝大多数使用场景,并满足绝大多数道德诉求和雄心壮志。
末了,我想感谢自由软件基金会巨大的付出,我祝愿它和它两位无所畏惧的领袖Richard M. Stallman和John Sullivan在下一个三十年中再打一场漂亮的仗。去干吧!
上文是作者Jono Bacon发表在Opensource.com上的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30 years in
GNU和自由软件运动四十周年
自由软件基金会 (FSF) 于2023年9月27日发表文章庆祝 GNU 和自由软件运动四十年。
四十年后的今天,GNU 和自由软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虽然软件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但绝大多数用户无法完全控制它。自由软件的定义最初由 RMS 本人制定。但其初衷是尊重用户的自由,并且尊重整个社区。
FSF 执行董事 Zoë Kooyman 表示,GNU 不仅仅是基于自由软件的最广泛使用的操作系统,也是指导自由软件运动四十年的哲学理念的核心。他还说道,我们希望四十周年纪念能够激励更多黑客加入 GNU,实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创建、改进和共享自由软件的目标。如今,软件正在控制我们的世界,而 GNU 是对现状的批判和解决方案,我们亟需它来避免技术控制人类。
RMS 谈 AI、Red Hat 和道德软件许可
在2023年9月瑞士 Biel 举行的庆祝 GNU 诞生 40 周年的活动上,GNU 和 FSF 创始人 Richard Stallman (RMS) 发表了 25 分钟的演讲,除了披露身患癌症外,他还谈论了 Red Hat、AI 和道德软件许可。

RMS 在瑞士 Biel 参加庆祝 GNU 40 岁生日的活动
他表示目前正在接受滤泡性淋巴瘤的治疗,称之为 “生长缓慢和可控的”。
Red Hat 和 GPL
Red Hat 的支持合同禁止客户重新分发该公司的开源软件,RMS 认为此举可能没有违反 GPL 许可,但其做法是 “反社会的”。他认为红帽公司应该停止这一做法,或者社区能通过施加影响力让 Red Hat 做出改变。
生成式 AI 不具备理解能力
对于 AI 或生成式聊天机器人 ChatGPT,RMS 认为危险主要来自于 AI 营销人员所编织的叙事。他认为今天的 AI 尚未真正具有理解能力,但人们正使用 AI 这一术语来夸大其词,他说 ChatGPT 生成的内容都是废话,不过是流畅的废话。因此他认为,相信 ChatGPT 这类产品生成的内容的人都很愚蠢。
RMS说道:“在我看来,‘intelligence’意味着需要具备了解或理解某个领域的能力。如果某些东西不能真正理解事情,我们不应该说它是智能的,甚至是一点智能都没有,但人们正在用人工智能一词来描述废话生成器。”所以他没有把那些产品称作 “人工智能” 或任何带有 ‘intelligence’ 一词的东西,因为这会鼓励大众认为它们(生成式人工智能程序)所说的不是胡说八道。它鼓励大众相信它们,这给了他们造成巨大伤害的机会。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 RMS 认为真正的人工智能并不存在。他补充到:“有些程序可以查看一些放大细胞的照片并告诉你诊断结果,无论是否患有癌症,比任何人类医生都更有可能正确。另外,有一些人工智能系统可以非常有效地找出什么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这些被反社交媒体平台使用,可悲的是,它们效果很好。他们非常擅长这些工作,但他们所做的是让用户上瘾。”
道德软件许可证
RMS 似乎不是所谓的 “道德” 软件许可证的支持者,试图监管谁可以使用软件。这不足为奇,因为他倡导的自由软件哲学的四项基本自由中的第一项是用户具有出于任何目的运行软件的自由。
演讲最后,RMS 抛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让年轻人对自由软件感兴趣?”他称这个问题是 “我们在社区中面临的难题之一”。
自由软件基金会迎来 40 周年:新任主席上任、推出 “LibrePhone” 计划
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FSF)在 2025 年 10 月迎来成立 40 周年纪念,并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领导层更替与全新自由软件项目的启动。

FSF 任命资深成员 Ian Kelling 为新任主席,他表示将带领基金会应对计算机用户自由面临的新挑战,并扩大自由软件运动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执行总监 Zoë Kooyman 公布了名为 “LibrePhone” 的新项目,目标是在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上实现完全自由的软件系统,为用户带来真正不受限制的计算体验。该项目由长期参与 GNU 开发的工程师 Rob Savoye 参与领导,被视为 FSF 推进 “移动端自由” 战略的重要一步。活动中,来自 EFF、F-Droid、Sugar Labs 等组织的代表共同讨论了自由软件、隐私保护及教育应用的未来合作方向。
FSF 表示,未来将进一步支持全球的地方性自由软件社区(LibreLocal),继续推动用户 “使用、学习、修改与分发” 软件的权利。四十年后的今天,这一理念依旧是自由软件运动的核心。
